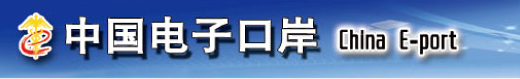10月初,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2国商贸部长宣布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此举标志着迈向占世界经济总量40%、贸易额1/3的自由贸易组织成型。不同于国内一边倒的“事后诸葛”的新闻评论,境外媒体对此次宣布较为谨慎,虽有附和之语,更多的是指出这一协议在各国议会、国会等立法部门受到阻挠最终难以生效的可能性,以及此举带给各成员国国内经济转型阵痛及社会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等的必然性。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正当性存疑,对中国过去十几年中依靠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成果还是要加以肯定。退一万步说,TPP即使达成,它也不是唯一一个区域性贸易组织,更不是唯一一个全球性贸易组织。且不说与其体量相当而且就当下看来政治意义也相近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还有双边自贸协定的存在,更有跨越半个多世纪风云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业已存在的贸易协定短期内仍大有前景。
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建立时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给成员带来的繁荣中再进一步,通过降低成员间贸易关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国各地区间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经济收敛。在全世界195个独立国家中,有161个是WTO的成员国,而其中150个都是发展中国家,说WTO是“富豪俱乐部”是不恰当的。作为WTO前身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国之一,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从1986年开始“复关”谈判,并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的成员。现在,WTO成员间的贸易额已经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97%,是名符其实的“经济联合国”。加入WTO以来的13年间,中国连续多年都是世界第一出口国。而且,中国也是TPP成员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了中国,WTO才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贸易组织;有了WTO,中国才享受了上个十年的大繁荣。这样说或许失之笼统,但其中涵义不言自明。
应该看到,新建立的双边和多变贸易伙伴关系都是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促进,贸易自由化也往往带来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人类福祉的改善,和技术成果的共享。按照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比较优势的存在,使得进行自由贸易的各方互利互惠,共同提高本国人民的福利。中国参与的WTO的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虽然贸易壁垒的存在大大延缓了世界向扁平化发展的速度,但不可否认,交流的意愿占据了主流,互通有无好过闭关锁国,互利互惠好过固步自封。
随着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出口进入慢车道,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多地强调产业结构改革和扩大居民消费,对国际贸易的兴趣从庙堂到坊间都在降温。加之各种带有老旧意识形态意味的贸易阴谋论,连中国的全球第三大、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都成了抵制对象,实在有失理智。
贸易是人类进步的强劲引擎。从丝路上的小镇悬泉到古希腊的城邦,从地中海南岸的亚历山大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布尔,从乌鲁木齐的大巴扎到北海沿岸的海牙,骆驼和商船运来的商品大大丰富了当地市场,而商人、传教士和书吏带来的宗教、文字和文化习俗也促进了世界各地思想的交流。虽然贸易也带来战争、奴役、瘟疫和侵占,但今天看来,即使最贫穷守旧的国家也对获得进步世界的商品和技术心向往之。也因为贸易,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获得了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秩序,多边谈判机制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在争端面前略可依凭的确定性。
作为是世界上最精通做生意的民族之一的中国人,在全球贸易的价值链中,需要担负起商品和服务提供商之外更大的责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中旬预测,亚洲地区仍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而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仍将是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加之经济体量和贸易网络的原因,对整个区域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也仍不可小觑。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该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大国义务,树立大国应有的形象,做负责任的大国。这也就意味着,从实力到心态,从动机到行为,从价值观到契约精神,中国都应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和改进。
中国也是大国。当年龙永图先生说服国民所用的“菜市场”中“小商贩”的比喻在今天已经很不合适:中国现在是大商场里的品牌店,早就不该再用小商小贩招徕顾客赚取利润的噱头,而更应该依托定位、品牌形象、营销,更重要的是创新,来合作共赢,而不仅仅是卖货。
短期看,三五年的时间内,TPP以及可能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不会对中国造成直接的影响,业已存在的WTO和已经将触角伸向全世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大大缓冲潜在的贸易孤立;此外,众多贸易协定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也将起到缓冲作用;更何况中国和TPP成员国的贸易关系拥有很大的惯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扭转。但眼光放长远,中国也应该警觉起来了。